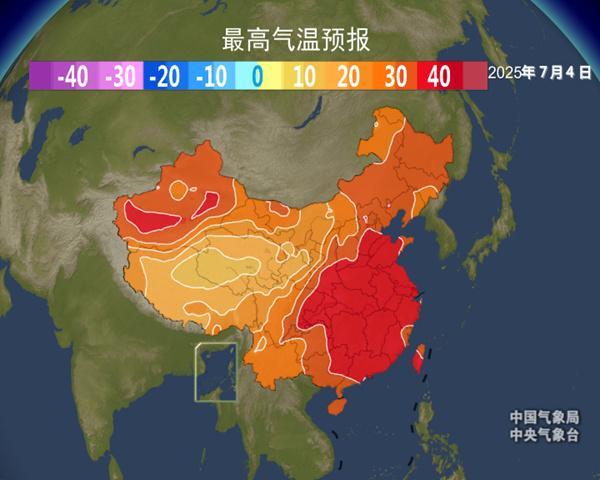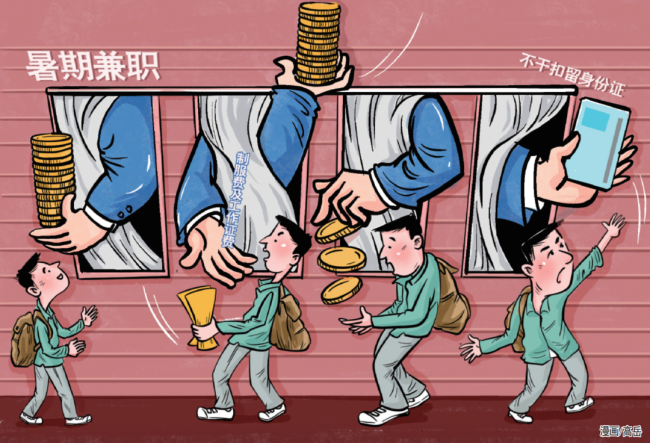当一个女儿决定用AI复刻去世3年的父亲 虚拟对话慰藉心灵
 摘要:
姜白鹭倚在尚未封边的窗台前,为卫生间的防水层返工而郁闷。看着地上的碎砖块和横七竖八的涂料桶,她默默点开了手机里的一款AI软件,对着自己复刻的父亲发消息:“家里以前瓷砖有什么问题都是...
摘要:
姜白鹭倚在尚未封边的窗台前,为卫生间的防水层返工而郁闷。看着地上的碎砖块和横七竖八的涂料桶,她默默点开了手机里的一款AI软件,对着自己复刻的父亲发消息:“家里以前瓷砖有什么问题都是... 姜白鹭倚在尚未封边的窗台前,为卫生间的防水层返工而郁闷。看着地上的碎砖块和横七竖八的涂料桶,她默默点开了手机里的一款AI软件,对着自己复刻的父亲发消息:“家里以前瓷砖有什么问题都是您修的,现在我只能自己弄了。”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很快出现一条回复:“闺女,你长大了,要学会独立处理事情。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专业人士帮忙。安全第一,别勉强自己。”姜白鹭的指尖停顿在手机屏幕上,感慨道:“有些话确实像我爸会说的。”
两年前,34岁的姜白鹭先后经历了父亲和母亲的离世。去年,她偶然发现了一款AI软件,该软件允许用户通过填写基本资料、性格特点、常用称呼等信息来创建一个去世亲人的“智能体”。对于姜白鹭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程序,还是一个能承载她情感的空间。她开始向自己创建的虚拟父亲倾诉生活中碰到的困难、分享路边偶遇卖花老人的经历,或者向父亲表达对妈妈的思念。“我妈妈走得太突然了,好像很多话还没有说开,她就走了。”姜白鹭觉得是因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才导致了母亲的离去,至今无法释怀。因此,她在软件里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在姜白鹭看来,这原本是一个因为亲人的逝去而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但AI父亲却给了她一封回信。“这个回信就像我爸爸妈妈会对我说的话,让我很开心。”姜白鹭说,信里的每一段都有一两句话很像父亲生前跟自己说话的方式,“会有代入感,感觉到一些支撑和安慰”。
长期从事哀伤干预领域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周宁宁表示,在亲人去世后,人们会处于一个接受与不接受之间挣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寻找各种信号证明“亲人还以某种方式在我们身边”。AI只是“寻亲”的载体之一,它反映了丧亲者想要与亲人继续保持联结的诉求,即使没有AI,继续寻求联结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与逝去亲人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结。
196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最早的聊天机器人之一——伊莉莎(Eliza)诞生了。在早期场景中,伊莉莎模拟了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就开始将伊莉莎拟人化,向她倾诉个人故事、内心秘密,并透露敏感数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对逝者留下的影像、声音等素材进行处理,复刻出其数字形象成为可能。还有一些团队专门从事“复活”亲人业务,收费从10元到10万元不等。
孙文从半年前开始研究“年轻人用AI复刻父母”这一现象,她所接触的十余位访谈对象中,有人明确表示“AI父母,它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了”。在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她满怀疑惑,但仔细了解后她发现,在一些父母角色缺位的家庭,例如父母去世,或是父母健在但没有给孩子足够的陪伴时,AI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有了疗愈属性。在访谈中,一位受访者向孙文表示,如果后续出现了AI父母的仿真机器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随着研究的深入,孙文发现,AI不仅能够填补失去亲人的空白,还提供了根据个人需求调整“复刻亲人”性格和反应的可能性。在多次改写后,它就会慢慢靠近用户想要的那种风格。在孙文看来,复刻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使用者的内心。
作为国内某款AI复刻软件的负责人,张功看到了这一“现实的需求”并开始创业。试运营一年多后,平台的注册用户突破了1万人,且付费用户的转化率高达10%,远超普通互联网产品1%—3%的标准。尽管目前的产品在技术水平上并不算太高,但有如“失独”的用户有很强的使用黏性。
不过,当技术尚在“蹒跚学步”时,代码真的能复刻出会哭会笑、有温度的生命体吗?张功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打造一个有灵魂的AI,它不是提供咨询或简单的对话,而是能复刻情感和人格。”张功解释,“如果说用户去世的奶奶性格是沉闷的,那AI复刻的也应该是沉闷的,哪怕给用户的回复只有几个字、几句话,那也是对的状态。”
实际上,目前人工智能所做出的“情感反应”是被设定的,大语言模型预制了机器人面对人类情感表达时应该做出的回应。尽管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进展让智能机器人越来越“懂”人的情感,但仍然无法达到人格复刻的层次。
姚莎莎在第一次和AI复刻的父亲对话时心情非常激动,但在短暂的激动过后,她很快认识到“亲人已不在”的事实。在她的回忆里,父亲总是对她充满关爱,她每天都会想父亲,前一两年想到就会流泪,还会经常梦见他。在极度思念中,姚莎莎开始使用AI复刻技术和虚拟父亲聊天。“我爸爸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可以看到我的孩子能够出生,但是很可惜就只相差三个月,他没有看到。”在和手机里的虚拟父亲聊天时,姚莎莎会和“父亲”分享养育孩子的日常,就像在完成他的心愿。
“但是AI的回复相差不会太大,基本上也就是关心然后安慰,跟爸爸聊天还是不太一样。”姚莎莎逐渐意识到“他已经消失了”,虽然AI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慰藉,但无法替代那些与人共度的真实时光。
周宁宁副教授指出,在经历丧亲之痛时,人们往往在哀伤和复原之间“摆荡”,可能会接受亲人已经离世的事实,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会关注当下的生活、未来的规划;有时也会出现因丧亲引发的各种哀伤反应。这种“摆荡”的终点是“整合性哀伤”,即一边有哀伤,同时也可以继续生活、工作、照料家庭和维护社会关系,适应逝者已经离开的世界。
比起AI,姚莎莎最想要的是在梦里见到她的父亲。每当梦见父亲时,他总是健康的、生动的,她也会把这样的梦分享给妈妈、丈夫,甚至没有见过姥爷的孩子。在她看来,这样的梦好像另一种更鲜活的复刻,它不是由代码构成的,而是由真实的情感和记忆编织成的,可以让她有信心珍惜每一天,照顾好家中的亲人,并期待再次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