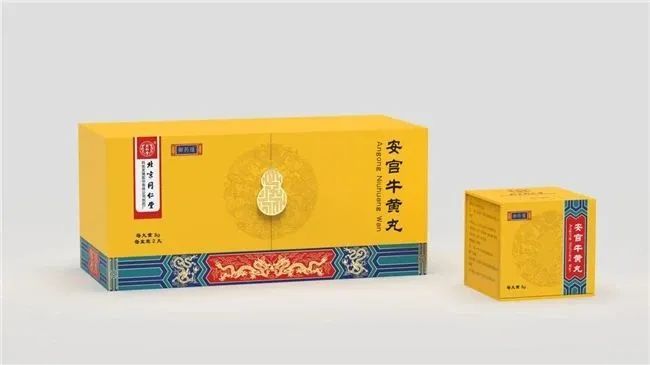九芝堂业绩双降国资管理层闪离迎新变局
九芝堂业绩出现双降,国资管理层出现变动,迎来新的变局,面对业绩压力,公司高层可能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优化措施,以改善业绩状况,此次管理层变动或许意味着公司正在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和策略,以应对市场竞争和业绩压力,九芝堂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内部管理和创新,以实现业绩的稳步增长,摘要字数在100-200字左右。
中医药行业历来流传“北有同仁堂,南有九芝堂”的说法。
但时过境迁,在市场化浪潮与行业变革的冲刷下,这一南北分庭抗礼的态势已被深刻重塑,两者在业绩规模、发展韧性上的差距正持续扩大。
近年来,同仁堂凭借稳定的战略布局稳居中药龙头位置,而九芝堂与同仁堂的营收规模差距已拉大近8倍。
近日,九芝堂披露的2025年上半年业绩数据仍难如人意:当期实现营业收入12.65亿元,同比下滑25%;扣非净利润1.36亿元,同比下滑28%,单季度表现更显承压——2025年第二季度扣非净利润降幅进一步扩大至57%。
雪上加霜的是,管理层的动荡为九芝堂的国资整合进程再添波折。2024年11月,黑龙江省国资委通过股权收购正式成为公司实控人,2025年5月,公司才刚完成“摘帽”、解除ST风险,仅一个月后,黑龙江国资委背景人员董事长孙光远、董事吕鸣与薄金锋便以“工作变动”为由密集提交辞呈。
在业绩下滑、治理动荡的多重夹击下,这家拥有374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将如何破局?
01 对赌前景承压,业绩颓势拉大目标缺口
九芝堂的前身是“劳九芝堂药铺”,最早可以追溯到清顺治七年,即公元1650年。
图 / 九芝堂公众号
现代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正式设立,次年便成功登陆深交所,开启了老字号的资本化征程。
此后二十余年间,九芝堂实控人经历了四次重要变更,每一次更迭都折射出这家老字号药企在资本浪潮中的转型挣扎。
2002年,长沙市属国资将九芝堂集团整体出售给湖南涌金等企业,“涌金系”创始人魏东通过间接持股成为实控人。
然而这一资本纽带在2008年遭遇重大变故——魏东自杀身亡,实控权随之转移至其妻子陈金霞手中。
2015年是九芝堂发展历程的重要分水岭。友博药业实控人李振国用15亿元获得九芝堂28.06%的股份,又以65亿元的资产估值将友博药业装入上市公司,凭借42.33%的股份,成为九芝堂实控人。
然而,到了2024年,兜兜转转中,九芝堂的实控人又回到国资手里。2024年11月,黑龙江省国资委旗下辰能创投以3.85亿元收购李振国所持6.25%股份,持股累计达24.04%成为九芝堂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国资委正式成为实控人。
股权交割后,李振国的角色发生微妙转变:虽让出实控权,但仍持有公司18.91%股份,稳居第二大股东之位,同时继续留任副董事长、总经理。
不过,这场国资接盘并非无附加条件,一份严苛的业绩对赌协议同步绑定李振国:他需承诺九芝堂2025-2027年扣非净利润总和不低于9亿元,若未达标,差额部分需以现金全额补偿。
要知道,2024年,公司扣非净利润仅1.8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三年九芝堂年均需完成超3亿元扣非净利润,较2024年水平需实现近70%的年均增长。
这一业绩目标,对李振国来说,压力不小。然而,2025年上半年,公司扣非净利润仅1.36亿元,同比下滑28%,不仅未呈现回暖态势,反而进一步拉大与对赌业绩目标的差距,李振国的现金补偿风险与日俱增。
02 国资背景管理层离场,入职未满一年密集辞职
不仅业绩承压,九芝堂的内部治理隐患亦同步爆发。
2024年4月,公司治理漏洞集中暴露:因原实控人李振国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子公司资金的违规行为,公司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监管规则,九芝堂股票随即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变更为"ST九芝",深交所随后对李振国及相关高管予以通报批评并记入诚信档案的处罚。
经过一年整改,直至2025年5月公司完成内控缺陷修复并满足监管要求,才得以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成功"摘帽"恢复正常交易状态。
但治理修复的成效尚未稳固,仅一个月后的6月27日,董事长孙光远、董事吕鸣与薄金锋便以"工作变动"为由集体辞任,彻底退出公司管理层。
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位核心高管均为黑龙江省国资委背景人员,其中,孙光远曾任黑龙江省国资委企业监督局局长、省产权交易集团董事长,三人于2024年7月通过董事会换届入职,肩负着国资入主后重构治理体系的核心使命。
未满一年的任期与密集辞职的动作,不仅折射出国资治理理念与企业原有经营模式的磨合困境,更让这家老字号药企的战略连贯性与内部稳定性面临新的考验。
治理动荡直接传导至经营端。2024年九芝堂业绩颓势持续加剧,全年营收仅23.7亿元,同比下滑20%;即便已通过缩减25%销售费用强力控本,归母净利润仍同比大跌27%至2.16亿元。
内部运营的隐性矛盾同步显现:2024年末员工人数增至3689人,同比增长4.8%,但人均薪酬却同比减少6%至12.7万元,人均创利更是大幅下滑31%。
2025年7月17日,九芝堂通过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王立峰为新任董事长,接替因“工作变动”辞职的孙光远。
从职业背景看,王立峰是黑龙江省国资系统的资深从业者,现任九芝堂董事长同时兼任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其职业生涯长期深耕产权交易与资本运营领域,曾任黑龙江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黑龙江省产权交易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
但缺乏医药行业直接经验也成为王立峰的潜在挑战,如何将产权交易经验转化为中药老字号的产品创新动能,将是其任期内的关键考验。
03 产品“多而不强”,核心竞争力存疑
若说业绩下滑与治理动荡是九芝堂陷入困局的“表症”,那么产品竞争力薄弱与研发转化滞后,便是其难以破局的“根源”,与同行企业对比,这一问题则暴露的更为明显。
中医药行业历来有“北有同仁堂,南有九芝堂”的说法。同仁堂自1669年(清康熙八年)创立以来,依托宫廷供药的传统积淀,奠定了北方御药典范的行业地位。
图 / 同仁堂公众号
九芝堂则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在长沙奠基,以“劳九芝堂药铺”之名深耕湖湘市井,其传统中药文化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二者曾共同勾勒出中医药行业南北呼应的经典格局。
但时过境迁,这一南北分庭抗礼的态势,在市场化浪潮与行业变革中已发生深刻重塑,两家老字号在业绩规模与产品竞争力上的差距持续扩大。
从业绩维度看,2024年同仁堂以186亿元营收实现4%的同比增长,即便受中药材价格上涨拖累,净利润同比下降8.5%至15亿元,仍稳固占据行业头部位置。
反观九芝堂,同期营收仅24亿元,同比下滑20%,归母净利润2亿元,同比降幅达27%,已连续两年呈现“营收、净利润双降”的颓势,规模差距较同仁堂已拉大近8倍。
产品竞争力的分化更为显著。同仁堂凭借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构建起强劲的市场壁垒,据浙商证券援引中康开思2023年统计数据,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在零售终端的市占率约48%,长期处于细分领域领先地位。
图 / 同仁堂公众号
九芝堂的产品则面临多重挑战,核心品种的政策受限尤为关键。
根据2025年1月起执行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其核心处方药疏血通注射液的医保支付范围,已从“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缩窄至“仅限急性脑梗塞患者”,且仍需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使用。
2024年前三季度,疏血通注射液销售额为4.99亿元,结合全年营收测算,该单品占比约24%,是公司重要的业绩支柱。然而,医保支付范围的收紧直接导致其适用人群大幅缩减,临床使用场景受限,后续销售规模面临明显压力。
从产品矩阵来看,九芝堂虽手握418个国家药品注册批文(含35个独家品种),覆盖OTC类、处方药类、大健康类三大系列,涉及心脑血管、补肾、补血、妇儿、五官科等多个领域,且2024年财报显示疏血通注射液、六味地黄丸、驴胶补血颗粒、足光散、逍遥丸、安宫牛黄丸等6个品种实现销售收入过亿,但“大而不强”的短板突出。
图 / 公司官网
除疏血通注射液受医保政策冲击持续下滑外,六味地黄丸、逍遥丸需直面同仁堂、仲景药业等品牌的竞争,尤其在集采政策下,价格战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安宫牛黄丸要与同仁堂、片仔癀等头部品牌争夺市场,终端存在感较弱;驴胶补血颗粒则面临东阿阿胶、福牌阿胶等企业的挤压,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
终端渠道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一差距。近日,「子弹财经」走访北京多家线下药店调研显示,九芝堂核心产品在终端市场的竞争力存疑。
有2家药店店员表示,店内未售卖九芝堂的安宫牛黄丸,主力销售的是同仁堂产品,且消费者对同仁堂的品牌认知度更高。
另外一款产品九芝堂驴胶补血颗粒售价145元/盒,但同类替代产品繁多,且价格相差不大,消费者选择空间大,进一步稀释了其市场份额。
图 / 九芝堂公众号
从数据上来看,2025年上半年,九芝堂存货周转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87.7天,升至331.6天,相当于库存商品要花近一年时间才能卖完,清晰暴露其存货消化能力下滑,经营端去库存难度持续加大。
研发层面,九芝堂在2025年上半年投入1.45亿元推进创新药研发,包括治疗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沉积症的药物、抗凝一类新药YB209、超级抗生素YB211等项目,同时开展疏血通注射液、驴胶补血颗粒、逍遥丸、玉竹膏、丹膝颗粒等已上市独家及重点产品的国家药品标准提升、有效性再评价等二次开发工作。
但创新药项目均处于早期临床阶段,干细胞治疗等前沿布局距离商业化落地更是尚需时日,短期内难以填补核心主力产品下滑留下的业绩缺口。
业绩下滑、治理动荡与对赌压力的叠加,再加上产品“大而不强”、研发转化滞后的短板,让拥有374年历史的九芝堂站在转型关键节点。
未来,新任董事长能否融合国资逻辑与医药行业特性,李振国将如何平衡对赌风险与创新让这家老字号重拾荣光,「子弹财经」将长期关注。